农村宅基地改革是事关农民利益、事关农村发展、事关乡村全面振兴以及城乡共同富裕的重大变革。为此,2020年中央有关部门在原有33个试点县(市、区)基础上,选择全国104个县(市、区)和3个设区市启动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绍兴被列为3个整市试点之一。在此背景下,绍兴出台《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坚持系统改革、问题导向和数字赋能,在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有偿退出、有偿使用等方面探索出“两完善、两健全、五探索”等一批具有县域特征的创新性制度。

从成效来看,绍兴经验中的“一码管宅”、“一张图”管理、数字化交易平台等具有较强的可示范性和可推广价值,但步入深水区的试点改革面临诸多痛点问题:
1.农户宅基地供需矛盾突出,无地可用与土地闲置现象并存
绍兴经济发展较快,地理位置优越,人多地少,宅基地供需矛盾突出。例如柯桥区钱清街道,自2018年规划管制以来整个街道行政区域已停止个人建房审批。部分青年等房结婚申请宅基地,但已无指标可用。目前全市大量信访、纠纷都有建房需求有关。与此同时,大量宅基地利用效率低下。由于历史积弊、政策变动、代际继承、人口流动等复杂因素,“一户多宅”、宅基地超标占用、长期闲置、腾退困难等现象较为普遍。据统计,各地村庄农户空置率约20%,部分地区空置率超40%。

2.农户“退宅”积极性不高,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有待完善
在城镇化背景下,户口在农村但工作生活在城镇所导致的人户不一致以及宅基地长期闲置问题大量存在。例如,在柯桥区开展的“以房换房”、“以房换钱”和“以房换租”三种宅基地退出方式中,有436户村民选择了“以房换房”,122户农户选择“以房换钱”,没有农户选择“以房换租”。从宅基地退出和置换的大数据来看,农户自愿“退宅”积极性不高,“地票”安置方式的观望态度较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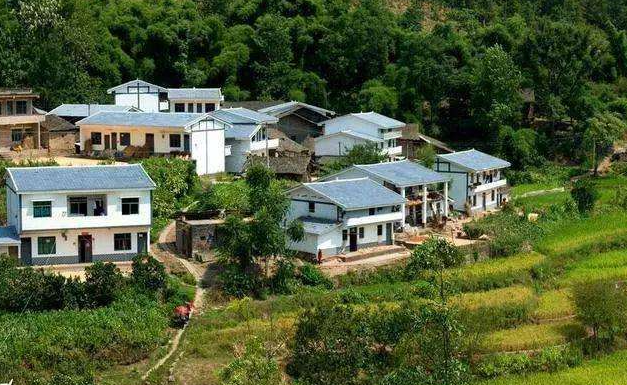
3.受制于估值难、处置难等困境,农房抵押贷款政策难以推广
农房价值评估是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的核心环节。由于尚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农房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缺乏有关农房抵押物的价值评估机构,相关评估规则尚不健全,导致农房实际价值难以评估。其次,目前农房产权证仅可用于金融机构贷款,不能用于交易过户,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受让人也仅限于本市农村宅基地资格权人,在农村“一户一宅”政策下,农村宅基地资格权人内部流转无法形成足够规模的交易市场,农房抵押物处置存在难以克服的实际困难。最后,从贷款利率风险定价来看,农房抵押物与普通农户信用贷款资产风险差异不大,金融机构盈利空间和业务拓展的积极性不足。目前全市农房抵押贷款余额仅3280万元,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导致了农房抵押不良贷款处置难题。例如,诸暨辖内银行共发生4笔农行抵押不良贷款,金额130万元,因流转困难至今无法处置。

4.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期限较短,不利于形成长期稳定投资
目前各地闲置宅基地和农房流转平台均规定农房流转租赁的最长流转期限为15-20年。从法理来看,城乡土地存在“同地不同权”问题;从实践来看,工商资本的回乡投资以及资金回笼往往需要较长周期,而流转期限太短必然制约工商资本长期扎根的投资积极性。调研发现,许多承租方前期的沉没成本很高,期盼农房租赁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期限能够更长,以稳定未来的投资预期。
5.试点改革缺乏法律支撑,“边缘革命”面临诸多法律风险
依法改革是理想,而“破法改革”往往是现实(即创新性改革倾向于突破现有法律的约束)。本次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并未得到人大授权调整相关法律,造成试点改革顾虑重重,从而使试点改革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初步分析表明,在绍兴宅基地改革新方案中,至少10处内容涉及“破法改革”问题。例如,建议暂时调整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关于宅基地的使用方案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办理”的规定,改为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会议或成员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暂时调整实施《物权法》第152条“关于宅基地使用权人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的规定,探索资格权人跨村跨镇建房的实施路径和办法;暂时停止实施《物权法》第184条、《担保法》第37条和《民法典》第399条“关于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规定,赋予农民住房财产权(含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融资功能等。
张雷宝教授认为农村宅基地改革重大而敏感,稳中求变、放宽搞活将是大方向,并从思想赋能、法律赋能、创新赋能、数字赋能等方面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1.思想赋能:全面把握中央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精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基本精神是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赋予农村宅基地完整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目前全省部分试点地区仍然囿于传统观念和体制约束,谨慎有余而探索不足。因此,建议全省试点地区有必要全面领会和把握中央有关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精神,即以《民法典》物权编基本原则为指导,坚持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拓宽农民财产收益渠道,优化农村人口土地空间配置。
2.法律赋能:授权试点地区可以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
改革现行不合理的农村宅基地制度,必然与现有法律规定发生一定的矛盾冲突。例如,2020年施行的新《土地管理法》规定,允许“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但没有宅基地“有偿使用”相关表述,这导致“有偿使用”被部分村民认定为乱收费行为,导致改革推行难问题。事实上,2015年全国33个县(市、区)启动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三项改革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曾授权试点地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就提供了一个依法改革的范例。为此,针对本轮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或省级人大在一定期限内允许试点地区可调整或暂不执行有关法律条款,防范“边缘改革”带来的法律风险。
3.创新赋能:探索“扩大流转范围、延长流转期限、放宽用途管制”的政策协同创新模式
创新赋能的本质是打破政策瓶颈的制约。具体建议:(1)打破宅基地使用权仅在宅基地资格权人内部的闭环流转旧格局,形成竞争性的城乡统一的住房市场流转新格局。赋予农村宅基地完整的用益物权和抵押物权,就必须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资格权人之外流转,在更大范围且以多元形式盘活农村闲置的宅基地资源,从而拓宽农民财产收入渠道,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适当延长农房租赁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期限。例如,在满足前置条件情况下,可允许宅基地流转期限为40年,进一步吸引乡贤、青年、农创客等人才下乡返乡,降低工商资本的投资顾虑。(3)建立农房抵押物价值评估机制。探索出台农房抵押物价值评估制度,建立由政府、司法部门和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抵押物处置协商机制,畅通农房抵押物处置渠道。(4)放宽农村宅基地用途管制(即允许闲置宅基地使用权入市)。尽管宅基地用途被严格限定为“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但全省越来越多的宅基地已经转变为经营性或复合性用途。例如,绍兴及全省各地的“闲置农房激活”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改革均扩展了宅基地的“经营性建设”用途,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之间的界限已经较为模糊。因此,建议逐步放宽农村宅基地的用途管制,淡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的界限,逐步打通农村各类建设用地之间的转换通道。
4.数字赋能:打造领跑全国的宅基地数字化治理“浙江样本”
宅基地治理的数字化平台,既是推进宅基地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深化宅基地改革的工具保障。因此,建议全省学习和推广绍兴宅基地数字化治理的实践经验,加大全域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实行“一码管宅”制,通过“一个数据库、一张图、一张表、一本台帐”(即“四个一”模式)使宅基地基础信息数字化。搭建全市域甚至全省域的宅基地数字化管理(交易)平台,实现农村“人、地、房”空间信息一体化、宅基地治理数字化、交易网络化以及服务高效化,最终打造领跑全国的农村宅基地数字化治理“浙江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