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社会组织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2021年3月,民政部等22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 净化社会组织生态空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随后各省市开展了打击非法社会组织的专项行动。如何从法律上进一步压缩非法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需要认真研究。

一、现状考察:非法社会组织危害严重
近年来,非法社会组织的危害性日益严重,具体表现为:
一是侵犯群众财产利益。很多非法社会组织打着“中国”“中华”“全球”等名头,利用人们对国字头等称号的信任,通过发证、颁奖、评比、培训等各种方式大肆敛财。遇到这样“高大上”的单位,人们往往愿意“慷慨解囊”。
二是影响社会稳定。如企图通过邪教和搞精神传销控制他人。这种洗脑性质的组织会让人丧失基本道德,严重危及社会秩序。例如在2014年“招远市‘全能神’邪教成员故意杀人案”中,邪教成员在麦当劳餐厅里传教,因被害人不愿意告诉电话号码就将其杀害,罪行令人发指。

三是损害社会公德。一些不法分子将自己包装成慈善家,打着“军民融合”“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疫情防控”等旗号,利用他人的善良,以公益之名行骗,严重损害了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公信力。
四是威胁国家安全。当前国际形势日渐复杂,为了经济和政治利益,一些非法社会组织充当外国政府的代言人,非法组织集会、游行,破坏我国的社会稳定。在香港暴乱、新疆棉花等事件中,都可以见到非法社会组织的身影。没有非法社会组织的介入,个别人很难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进行破坏活动。在自然灾害、意外事件发生后,一些非法社会组织也经常借题发挥,歪曲事实,煽动群众,破坏我国的社会稳定。
二、法律漏洞:治理非法社会组织的法律规制不足
虽然非法社会组织危害性严重,但我国法律对非法社会组织的治理措施,存在明显短板。

(一)行政法威力不足
当前,我国对社会组织的管理,除了少数行政法规之外,主要是依靠很多效力层级较低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规范效力未明的政策,缺乏综合性的《社团法》或《社会组织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法律依据严重不足。
首先,民政部的取缔措施强制力较低,难以起到威慑作用。作为登记关管理机关,民政部负责“取缔”非法社会组织,但这种执法手段象征性有余而强制力不足。2000年民政部《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第9条规定:“对经调查认定的非法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取缔决定,宣布该组织为非法,并予以公告。”显然,取缔主要是一种宣告性执法措施,即在程序上告知其系非法社会组织,缺乏实质性性处罚内容,更无法直接处理组织者。
其次,拘留等行政处罚的威慑力有限。对非法社会组织,可以处以拘留等行政处罚。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一)违反国家规定,未经注册登记,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被取缔后,仍进行活动的;(二)被依法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仍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可以“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但问题在于,很多非法社会组织用“国字号”招牌可以谋取巨额利益,15日拘留的惩罚力度较低,很难让其彻底解散。而且,公安机关进行行政处罚时不能采用刑事侦查措施,无法深挖背后的利益链条,而非法社会组织的名义负责人往往是“白手套”,实际控制人常隐藏很深。例如,2018年广州市民政局处理的“全球生命疗养联合会”,就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收取高额费用,非法敛财,对类似非法社会组织单凭行政手段很难进行溯源治理。
(二)刑法对非法社会组织存在盲区
在治理非法社会组织的文件中,经常会出现“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表述。然而,实践中却很难追究非法社会组织的刑事责任。
首先,司法机关很难将非法社会组织的敛财行为认定为诈骗罪。成立诈骗罪需要“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财产损失”等条件,而一些非法社会组织的敛财行为很难同时符合这些条件。常见情形包括:一是被害人被洗脑,不愿意承认被骗,即“心甘情愿被骗”;二是交钱者基于隐私等考虑不愿意报警、不配合调查,即“权当做公益、买教训了”;三是非法社会组织都有规避法律的意识,如以培训费、会议费等名义牟利,而培训和会议确实存在,此时就很难认定“财产损失”,无法成立诈骗罪。因此,在实践中,多数非法社会组织的敛财行为都没有被认定为诈骗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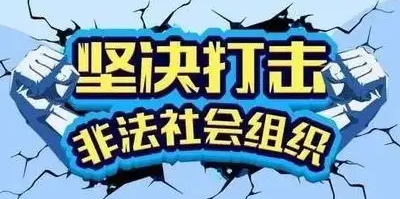
其次,我国《刑法》并未直接规定对非法社会组织的刑事责任。我国《刑法》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但多数非法社会组织不是上述组织。一方面,一些非法社会组织具有影响国家安全的政治目的,但不属于恐怖组织、黑社会或邪教组织,如2018年北京市民政局取缔的“中华民联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一些非法社会组织影响的是国家机关的权威性,这些山寨组织通过文字游戏,冠以“委员会”“发展局”“中心”等名称,包装成“准政府”或事业单位。按照我国《刑法》,“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属于招摇撞骗罪。虽然这些非法社会组织给人感觉像政府机构,但没有对应的国家机关,无法被认定为招摇撞骗罪。
三、对策建议:增设非法结社罪的立法建议
为打击非法社会组织,填补立法漏洞,笔者建议在《刑法》第296条“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后增设“非法结社罪”,具体表述为:
“非法社会组织在被依法取缔,受到行政处罚后,多次开展非法活动,谋取非法利益,情节严重的,对负责人和实际控制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从国际环境及我国非法社会组织的现状看,设立此罪极为必要。
(一)西方很多国家(地区)有类似罪名
现代国家有效控制了个体犯罪的危害性,但打击有组织犯罪的难度要大得多。非法社会组织是产生有组织犯罪的土壤,很多国家(地区)都通过刑法打击非法结社行为。有地区(国家)将非法结社规定为轻罪或治安罪,如在香港地区刑法中,非法结社罪属于妨害社会治安罪的一种。
很多国家则在《刑法典》中将非法结社规定为重罪。例如,《德国刑法典》第85条规定了“违反禁止结社罪”,即如果维护“某一社团,因违反宪法秩序或违反国际协调的意思而被无可辩驳地被禁止,或者被无可指责地确认为此种被禁止的社团的替代组织”,即可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罚金刑。《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246条也规定了“对国家有害的结社罪”。《法国刑法典》第五编专门规定了“参加坏人结社罪”,并规定了最高5年监禁刑并科75000欧元罚金。《意大利刑法典》第270条规定,对“颠覆性结社”处予5年至12年有期徒刑,对“以恐怖主义和颠覆民主秩序为目的的结社”,处以7年至15年有期徒刑;对“反民族结社”,处以6个月至2年有期徒刑。从各国立法趋势来看,增设“非法结社罪”符合现代刑法“打早打小”的积极预防主义。
(二)填补立法漏洞,保持罪名间的协调
我国《刑法》规定了“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但没有规定“非法结社罪”。根据我国《宪法》第35 条,“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属于并列的公民权利,有权利就有边界,我国《刑法》已经将“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规定为了犯罪,但没有规制非法结社,存在立法漏洞。
相较于“非法集会、游行、示威”,非法结社的危害性更大。一些非法社会组织频繁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行为,港独、藏独、疆独骚乱等事件的背后都有非法社会组织的影子,它们通过资金支持、行动策划等方式,为非法游行、示威等活动提供幕后支持。换言之,非法集会、游行、示威只是表面现象,而背后的非法社会组织才是根源。长期以来,对于境外社会组织在我国境内非法从事活动,我国法律缺乏严厉制裁措施,导致其肆无忌惮地从事反华活动。刑法应当标本兼治,将类似非法社会组织纳入打击范围,维护国家安全。
(三)严格限定适用范围,确保刑法谦抑性
治理非法社会组织,主要应适用行政法,不能过度依赖刑法。因此,应当严格限制非法结社罪的入罪门槛,具体包括:
一是设立行政违法的前置条件,坚持“行政法先行”。动用刑法是因为行政法失灵,成立本罪的前提是已经用尽行政手段,即非法社会组织“被依法取缔”“受到行政处罚”。只有行政处罚无效后,才可以动用刑法。
二是缩小处罚范围,将“多次”作为入罪条件。“多次”应限定为“一年内三次”,如果非法社会组织受到行政处罚后只开展了一、二次活动,可以再次给予行政处罚而无需动用刑法,刑法打击的是长期性、组织化的非法活动。当然,非法社会组织被取缔后,为了逃避处罚而更换负责人或者名称,但组织体系、活动内容相同,也属于“多次”。
三是排除程序违法的刑事可罚性,将“开展非法活动”“谋取非法利益”作为入罪条件。实践中,有些非法社会组织只是因为没有履行登记程序。例如,“梅州市蓝天救援队”在2018年未经登记而开展活动,但其活动内容是帮助群众,并无违法行为,后被政府吸收到梅州市应急志愿者协会,这种单纯程序违法的社会组织不是刑法打击的对象。同样,在筹备期间开展筹备工作以外活动的社会组织,如无证的非法校外培训机构和非法民办养老机构,都不是本罪主体。换言之,刑法上的非法社会组织,不仅要程序违法——未登记,更要实体违法——活动内容非法。
四是设立情节犯模式,将“情节严重”作为入罪门槛。“情节严重”的具体标准包括:获取非法利益30万以上、活动内容包括多个违法事实等。我国《刑法》对恐怖组织、黑社会组织等采用了行为犯模式,任何人只要成立类似组织即构成犯罪。但是,一般而言,非法社会组织并非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唯一目的,与恐怖组织等有本质区别,将“情节严重”作为入罪标准,更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五是降低法定刑,将本罪归入轻罪。如果非法社会组织从事了诈骗、非法经营等行为,可以直接认定为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如果非法社会组织成为了恐怖组织、黑社会等,也可以按照相应罪名定罪。换言之,非法结社罪是兜底性罪名,主要打击无法按照其他犯罪处理的情形,属于违反秩序的轻罪。
总之,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刑法应当有所作为。对非法社会组织需要综合治理、多管齐下。虽然主要治理措施是行政手段,但在行政措施失灵后,刑法应当发挥后盾法的功能,打击严重危害公共利益的非法社会组织。只有根治那些假大空的非法社会组织,才能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
(本文作者为高艳东,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

